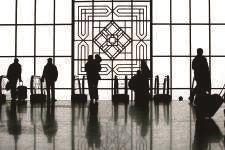别了,故乡
□黑子 从归心似箭的期待,到近乡情怯的忐忑,随着故乡的临近,这种感觉也愈发强烈。 弹指一挥间,40余载似水流年,昔日离乡懵懂无知;今日归来,景如旧,人已非,情之切,如孩童奔母。 故乡是熟悉的,每家每户,甚至每棵树每堵墙都了然于胸,但那是过往的曾经。故乡是陌生的,眼前的景物、房前屋后的村人,与镌刻在脑海中的样子,已无半分重叠。 我的故乡,与东北平原上其他的村屯长着同一张脸,但这里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,是心底最柔软的角落,是永远不变的心灵家园。 昔日呼唤我乳名的长辈,如今已难觅身影,老邻旧居也早已各奔东西,儿时的玩伴儿也大多断了音讯。何时再见他们? “小南沟”是我来到故乡的第一站。这里距离我家大约三五百米,只是一个约一亩大小的小水洼,但这里却是我儿时的乐园,记录了我童年一多半的快乐时光,如同“百草园”与童年的迅哥儿一样。春天和玩伴在这里挖婆婆丁;夏天在这里逮蚂蚱、捉蝈蝈、扑蝴蝶,天热时还去水里扑通两圈儿,但其实水很浅,最深的地方也就刚过肚皮,大多时“出水方知两脚泥”;秋天时和小伙伴儿一起,烧得金黄的苞米让我们一群淘孩子直吞口水,最开心的莫过于大家在“麻籽拍豆香”的乱吼声里相互打闹;冬天,我们在这里的冰面上打出溜滑,玩冰车儿,记得有一次我后脑勺结结实实摔在冰面上,迷糊、呕吐,在炕上躺了两天才爬起来,愣是不敢告诉大人咋弄的,怕挨揍。 离开小南沟,我向“家”走去。记忆深处“家”的样子已荡然无存,好在有参照物——水泥电线杆和变压器,这些早年就有,在参照对比下,大致能推断出当年家的位置。 当年我家的园子里有棵大柳树,整个村子前面只此一棵,离老远就能看见,树干笔直,树冠如伞盖,就如同三国时刘备家的桑树一样。春天,临睡前我爬上树,把捕鸟的夹子挂在树枝上,早晨起来必定有收获,那时的孩子以捕鸟为乐,根本没有啥生态保护意识,天热的时候,我和小伙伴就聚在树下的阴凉处玩耍。我自嘲地想,如果我们不搬家,大柳树仍在,是不是我家也会出“贵人”,我就如项羽般衣锦还乡,而不是像现在这样,村人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?这样想着,我围着“家”的房前屋后转了两圈,后来感觉好像有几个村里人都疑惑地向这里张望,于是我便沿着村路向别处走去。 村西头,我就读三年的启蒙学校,早已踪迹皆无。每家每户,已是旧貌换新颜,与我是陌生的。过往的一切因熟悉而亲切,如今的陌生让人感觉心里的距离很远。这时我才真正懂得“故乡容不下肉身,他乡容不下灵魂”的真正含义。 随意漫步在故乡的大街小巷,偶尔与村里人走个对面,也无任何交流,我对他们而言就是个外地人。我只问了一下路,打听小卖店,因为我要给老叔买纸上坟;向店主询问了一个人,我的启蒙老师,得知他早已故去。在我多年的读书时光里,教过我的老师约有百人以上,让我念念不忘的,唯有启蒙恩师,早就想给他敬杯茶,递一支烟,但先生已去,愿未了,空遗憾。 离开故乡时,我一再回首,边挥手边喃喃自语“别了,我的故乡。”也许没有再见,徐志摩诗代表了我此刻的心境,轻轻地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地来,挥一挥衣袖,不带走一片云彩……